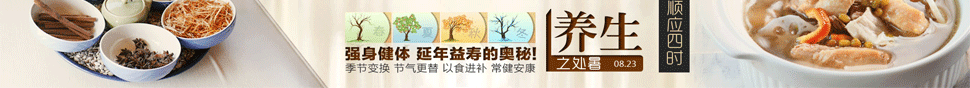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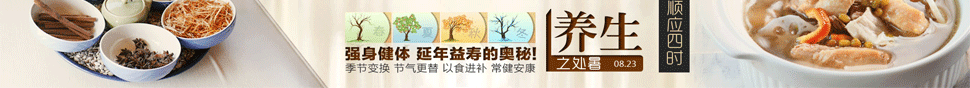
《西游记》以邵雍的“一元之数”为开头,讲了天地万物生成的哲理。在第九回又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叙述,它说长安城外有一个渔翁叫张稍,一个樵夫叫李定。一天,渔樵二人各携一瓶酒在泾河岸边散步,渔翁说:
“李兄,我想那争名的,因名丧体;夺利的,为利亡身;受爵的,抱虎而眠;承恩的,袖蛇而走。算起来,不如我们水秀山青,逍遥自在,甘淡薄,随缘而过。”
樵夫表示认同,接着他俩就“水秀”好还是“山青”好进行了争论。渔翁说以“无荣无辱无烦恼”之乐,樵夫对以“逍遥四季无人管”之欢;渔翁又夸以“无忧虑”之幸,樵夫还以“无利害”之福。最后二人联诗两首,共话山水之乐。
这段文字与小说主线关系不大,在清朝版本的《西游记》中甚至还被删掉了,一般读者也只是把它们当作诗词来看,其实作者在这里复诉了邵雍的处世哲学,要想弄懂它,就得了解《渔樵问对》。
渔樵相对话山水邵雍与《渔樵问对》朱熹曾对弟子说:“康节之学,其骨髓在《皇极经世》,其花草便是诗。”当我们读完《皇极经世》后,就已经完整的接触到了邵雍的体系。《皇极经世》第一部分“元会运世”是邵雍的“经世”之学,后面的《观物内篇》则是他的义理之学,而《观物外篇》属于易数之学,最后《先天图》作为基础,贯穿于各个部分。
除了《皇极经世》以外,邵雍还有《伊川击壤集》、《无名公传》和《渔樵问对》流传于世。《伊川击壤集》里除大部分的抒情诗外,还有不少说理诗,可以作为研究邵雍道学的辅佐材料;《无名公传》类似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是邵雍写的一篇小自传,里面说:
“能造万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极也,太极者其可得而名者乎?可得而知乎?故强名之曰‘太极’,太极者其无名之谓乎?”
这跟《老子》的“无名,为天地之始”、“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相同,认为本体是不可名状的。但《无名公传》最后又说:
“不佞禅伯,不谀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业儒,口未尝不道儒言,身未尝不行儒行。”
俨然以儒者自居,这再次说明杂儒道为一是邵雍体系的特点,他说“老子得《易》之体,孟子的《易》之用”,言外之意便是“以道为体,以儒为用”了。
黄百家编《宋元学案》时,认为《渔樵问对》非邵雍所作,而是邵伯温得家学以附益之,并说这篇文字显得“肤浅”。不过黄百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渔樵问对》是邵伯温的作品,他先是主观的觉得这篇文字“肤浅”,然后再推断说邵雍水平那么高,不可能写出这么“肤浅”的作品,因此这本书是“伪书”。可是,所谓的“肤浅”,只是他自己的主观看法而已,并不等于现实,这种逻辑毛病也常常在民国考证大师们身上发作,他们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偏好出发。
朱熹曾说:“康节《渔樵问对》、《无名公序》与一两篇书,次第将来刊成一集。”这说明朱熹认可《渔樵问对》是邵雍的作品,这篇文字通过渔者与樵者的问答形式,较为通俗的阐述哲理,应算是邵雍道学中最容易理解的部分了。全文杂糅了《伊川击壤集》的序和《观物篇》的内容,可能是邵雍晚年一以贯之的作品,我们只取没讲过的地方来说。
《渔樵问对》利害关系不可分离,无处不在《渔樵问对》的开头,樵者问渔者,鱼贪饵之利而受害,人贪钓之利为什么却能蒙利?既然大家都是为利而动,结果为何不同?
渔者于是进行了辨析,说:“子知其小,未知其大。”
樵者把利害关系简单的对立了起来,故而没有看到,对于鱼来说,吃到饵是利,被钓上钩是害。可是,假如鱼整天都找不到食物吃,那么这样的害不是更大吗?相比于饿死,冒险吃饵的害处不是要小些吗?对于人来说,钓到鱼是利,吃鱼也是利,似乎钓鱼有利而无害。可是,如果人整天都在钓鱼,却一条也钓不到,又没时间去干其他的营生,没有收入,这不也是大害吗?假如还要冒险出海捕捞的话,害就更大了。因此,钓鱼就像吃饵一样,得冒着受害的危险去钓。利害关系不可分离,无处不在。故云:
“鱼利乎水,人利乎陆,水与陆异,其利一也;鱼害乎饵,人害乎财,饵与财异,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
利与害属于“同出而异名”者,它们既对立又统一。鱼之利害寄于饵,人之利害寄于财。鱼如果不与人争饵,怎么会受害?散户如果不与庄家争财,害又从何而来?故知,争是从利转化为害的中介,所以《老子》说:“夫唯不争,故无尤。”财富其实是靠创造出来的,并不是靠争取而夺得的。夺得之物,岂能长保乎?
反过来,让是从害转化为利的中介,人相向而行,左右相让,则畅通无阻;鱼倏忽水中,先后有序,则能鱼贯而行。因此,邵雍说:
“夫义者,让之本也;利者,争之端也。让则有仁,争则有害。仁与害,何相去之远也!”
让不仅将害转化为利,而且还得仁;而争如果只是为了利,就可能害义。孟子见梁惠王的第一句话是:“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世人皆笑其迂腐,可是义乃是利的基础,只有义才能让,进而使害转化为利。
相反,如果只追求利,而不讲义,那么父子跟路人就没有什么区别,都只是利益关系而已。更糟的情况是臣为利而弑君、子
为利而弑父,故邵雍曰:“利不以义,则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追求利益一定要基于道义。
这便是《渔樵问对》里的义利之辨。
“有利”并不等于“有用”樵者又问,鱼得烹饪之后才能吃,这是不是说明自己的木柴对渔者有用?如果没有木柴,鱼是否因不能吃而无用?
对此,渔者回答说:“子知子之薪,能济吾之鱼,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济吾之鱼也。”木柴对于鱼的用处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火,假使木柴因淋湿而不能生火,那么它对于烹饪也就从有用转化成了无用。因此,木柴是“体”,火才是“用”。
火依附于燃料之上,燃料得火才有用,火得燃料才有体;水无形无状,以浸润为用,浸润以水为体。因此,火属于用,水属于体,火可以使邻近的水变热,水却不能够使邻近的火变冷,这是因为体用有别的缘故。所以说,有体必有用,但是体不等于用,用也不等于体。
世人都认为有利就会有用,而被人利用就是受害,因此“用生于利,体生于害。”但是我们已经论证过,利与害是不可分离的,故而体与用也不能分开。世人愚钝,没有弄明白有体必有用的道理,因而才执着于“有用”跟“无用”之间的对立,看不到它们的统一,故而误以为某些事物一无是处。
《老子》曰:“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人们执着于有形有状之物,认为它们于己有利,就如樵夫执着于木柴一样;可是如果没有无形无状之物,没有火,那么有利的木柴也就没有用处。盘子的外表再精致,如果不是空心,就不能装东西;房子的外墙再华丽,如果没有内部空间,也不能住人。人们在盲目逐利的时候,是否也应该想一想:这对于自己有没有用?
“名”与“实”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樵者出柴,渔者出鱼,二人烹鱼而食,之后在伊水边散步,讨论《周易》。这部分的内容与《观物内篇》一样,因此我们略过不谈。
之后他们又谈论了名实问题,渔者说:
“夫名也者,实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于不足,利丧于有余,实丧不足。此理之常也。”
购买专栏解锁剩余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