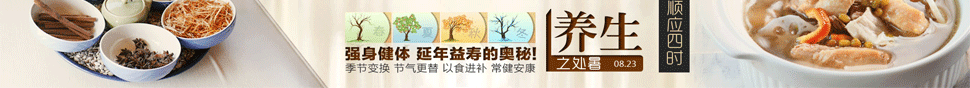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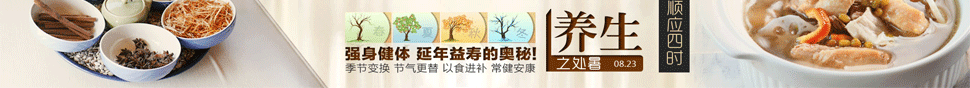
潘向黎(图源:北京日报副刊)
文
潘向黎
文学博士,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上海市作协副主席。
代表作:长篇小说《穿心莲》、短篇小说集《白水青菜》等
周末长文字。读完此文许久可以不用再读泉州了,因为此篇“营养”实在太充足了。
泉州,泉州
回泉州了。回故乡的感觉,首先是听觉的。耳朵灌进了久违的乡音,首先竟是微微的刺痛,像塞进了苍耳一类带有茸毛软刺的小球球,刺痛伴随着微痒,还有酥麻,继而,转为一种由弱而强的抚慰。不知为什么,鼻子就会发酸,表面上维持着不动声色,心里翻腾起了一种带着委屈的温暖,或者说带着温暖的委屈,仿佛有一个在心的角落蜷缩着身子的小孩子突然站了起来,大声喊:“人家一个人,等了这么久!”听到乡音,才深切明白自己平时的身份或者说处境,原来是一个游子,在现在生活的城市,再怎么安居乐业,或者熬成也无风雨也无晴,终究是一个异乡人。是的,我在上海生活了三十多年,始终是一个异乡人。
回到家乡,得到抚慰的,其次是视觉。蓝天白云下,红砖红墙和浓绿的树冠照样鲜明,合欢花、三角梅、刺桐花、凤凰花、凌霄花、月季花……将殷红、朱红、紫红、橙红、粉红、玫红,毫不吝啬地泼洒得到处都是,像久别重逢、掏心掏肺的热情。
味觉。蚵仔煎,鸡卷,面线糊(钟楼下那个老伯开的那家最好吃),肉粽(钟楼下那个老婆婆家的最好吃),绿豆饼(当然是正泉茂的啦,而且要当天出品的,好几次,表哥送来都说,还是热的呢),贡糖(对需要控制体重的人,这款美味太“反社会”啦),各种蟹,各种鱼,各种蛤,各种螺,还有各种糕点,其中有我最爱的碗糕……
听觉、视觉、味觉被抚慰的全过程,心理的满足也伴随始终,但心理更主要的满足来自与亲人的见面。家族的全盛期大概是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吧,之后,长辈们渐渐衰老了,平辈们出国走了好几家,再后来,回家一次黯然一次:上次回来,还住在二姨家呢,这次已经见不到二姨了;上次回来,二姨虽然走了,至少大姨还在,这次连大姨也不在了。这是时光。这位公正的主宰,馈赠我无数宝物、无数美好,也淡然地剥夺了曾经有过的许多欢乐和温暖。
我以为我的返乡,大概就是重复失落与寻觅,伤感与珍惜的主题了。但是,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些密码,地缘的、历史的、文化的密码,埋在生命的深处隐密的角落,自己也长久浑然不觉,但是密码是在那里的,时间的齿轮转动,到某一天某一时刻,机缘的火花掠过,那个密码像烟花一样被点燃,喷发出满天惊奇和感慨。
对我来说,已经发现的密码有:大海、泉州港。
生活在泉州和上海,说起来都是在海边,但其实生活里很少感觉到海的存在,一方面不是随时看得见海,另一方面是即使看到了,那个颜色也和心目中的蔚蓝相去太远,以至于从未发出任何赞叹。黄浊的、不能让人赞叹的海,还算是海吗?因此,我这个理论上在海边长大、在海边生活的人,对大海怀着永远的乡愁。在日本的旅行,饱看太平洋,成了最大的收获。太平洋,真是“洋”啊,看得物我两忘,看得心满意足。
图源:陈陈
但,虽然就生在泉州,小时候,我并不知道泉州曾经的繁华和荣光,即使在长辈们的口中也很少听说。“却顾所来径,苍茫横翠微。”对家乡的历史,有多少人真正清楚?对自己的生命的源头,有多少人真正了然于心?
这次采风,我的心情和任何一次采风都不一样,好像面对一个祖先留下的洞窟,热切盼望又不无忐忑,用“海上丝绸之路”的钥匙,开启洞窟之门,我们走了进去,面对无数宝藏,目瞪口呆,目眩神迷。
有时候开玩笑,我会自称“南蛮子”(这是清朝满人对南方汉人的蔑称),但其实我们这些“南蛮子”,都是宋代以后从中原迁徙到福建的,福建最早的原住民,是闽越族。
图源:猫饼制造
闽越族是古代东方少数民族之一,以福建为主要居住地。闽越人的生活离不开水与海,因此他们善于造船,很早就开始航海,并且和日本、东南亚进行海上贸易。船棺葬、蛇图腾崇拜、纹身、鸡卜等带神秘色彩的民俗,其实都与水上活动密切相关。比如纹身,就是长年在海边生活的他们,用它避蛟龙之害。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看到的外形似鸟的船,是在别处从未见过的,这些造型奇异的船默默验证着历史上关于福建人的记载:“……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汉书》)。”“(闽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越绝书》)。”
以船为车,以海为路,在海上自如往来,带来了生活方式的改变。考古发现,在秦汉时期,福建已经使用燃烧香料木的香熏了,而这些香料木,正是从东南亚、南亚诸国舶来的。舶来品,“舶”,航海大船也。一个舶字,明白无疑地告诉我们:进口货,最早都是从海路上来的。而纹身的习俗,到了宋元时代大放光彩,泉州纹身的技艺非常出名,吸引了许多外国人来泉州纹身。马可·波罗就说,有许多印度富人到刺桐城(泉州古称)来纹身。元朝的《岛夷志略》中载:“(外国)男子尝附舶至泉州经纪,罄其资囊,以文其身。”这狂热与今天的嗜美一族斥巨资赴韩国整容、去欧洲注射美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唐·包何《送李使君赴泉州》)。”“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唐·薛能诗)。”唐朝不愧叫作“盛唐”,民族交融带来的健旺血气、泱泱大国的自信心态,使得中国真正是个开放、自由而强盛的国度。在唐朝,今天被称之为“小小的”的泉州,成为中国四大对外贸易港之一。五代时留从效扩泉州城,“重加版筑,旁植刺桐环绕”,俏丽浓妍的刺桐花从此在泉州处处盛开,泉州“刺桐为城”,泉州港也以“刺桐”的音译“Zaitun”闻名海外。
上苍何意,为什么是泉州——刺桐?
地理上是因为南方沿海多山,山地使沿海和内陆交通不便,加上当时的地方诸侯也需要海外资源来支持地方经济和自己的权威,于是自然而然转向海路的开拓。唐中后期,陆上的丝绸之路因战乱而阻断,加上经济重心的南移,“海上丝绸之路”应运而生。“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这是南宋吴自牧《梦粱录》里明晰的记录。
北宋初年,泉州已经是全国三大海港之一了,到中期,成为仅次于广州的第二大港,北宋末年南宋初,已经和广州并驾齐驱。元代,“刺桐港是世界最大的海港(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语)。”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
季风也是泉州的好朋友。秦汉起,东南沿海已经利用风帆和季风出海。唐宋两代,对季风的了解渐渐深入,利用得日益娴熟——“船舶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朱彧《萍洲可谈》)。”即:东南亚太平洋航线和南亚印度洋航线,利用太平洋、印度洋夏季所吹的东南风和冬季所刮的西北风。王十朋诗谓:“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也是当时人娴熟利用季风的明证。而今天泉州尚存的九日山祈风石刻,就是当时泉州地区祈神保佑出海顺风的官方典礼的遗迹。
当地造船业发达。闽越人自古善造船,而且在原料方面也占尽地利——“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船又次之(宋人吕颐浩《忠穆集》卷二《舟楫之利》)。”宋元时代,泉州造船业空前兴盛,《太平寰宇记》甚至将“海舶”列入泉州特产,可见其盛况。海船作为一个地方的特产,实在超乎想象。我的脑海里闪过,在牡蛎干、紫菜和绿豆饼的队列后面,突然出现几艘巨大的海船,忍不住笑了起来。但是,这项吃不进嘴,也送不了朋友的特产,本事和名气都十分了得,而且是当时人人皆知的常识——“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宋·谢履《泉南歌》)。”
这两句诗,现在就镌刻在泉州湾古船陈列馆进门的柱子上。就在那里,我第一次和那艘著名的南宋古船劈头相逢。在浅蓝色池子内,多年前的古船静默矗立,气势摄人,似乎在等待船长一声呼唤,船员们马上起铁锚、扬篾帆,就可以乘风破浪,驶向远海。一个对泉州的历史始终缺乏实感的泉州人,实在很难用语言描摹那一刻的心理感受,好像过去的整个刺桐港,我从来不曾见过,连在梦里也不曾出现的古泉州,突然从水底浮了出来,飞升起来,出现在我面前。活生生的,气势磅礴。
这艘古沉船残长24.2米,残宽9.15米,复原后长达34米、宽11米,排水量近吨,载重吨——这在当时不算特别大的,大概只能算中等,但已经相当于唐代“陆上丝绸之路”多头骆驼的总运量了。因此随着贸易量的增大,品种的增多,对运输成本的考量日益重要,人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海船优于骆驼,海路便于陆路,因此,即使陆地上没有发生战乱,“海上丝绸之路”的优势也会日益显现出来。
看完大小,再看船型,这是一艘首部尖、尾部宽、船身扁阔、船底削尖,呈V字型的海船。这就是当时代表世界造船最高水平的“福船”的典型。这种“上平如衡,下侧如刀”的船型设计,兼顾了稳定性、快速性、耐波性和加工工艺等多项性能。更令人惊叹的是,这艘古船采取水密隔仓技术,即用隔舱板将古船舱体分成13个独立舱区。远洋航行中,即使一两个舱区破损进水,也不会影响其他舱区。后来这一技术被马可·波罗介绍到西方,水密隔舱技术逐渐被世界各国的造船界普遍采用。
泉州宋船数字化轮廓图(海交馆)
船仓里发现的各种香料,令人惊叹它们在水底沉睡了几百年,依然安然无恙,而当时船上的人估计大多未能从那场海难中逃脱。万物之灵的人的生命,远远比没有灵性的货物脆弱,思之令人悲凄。但那些造船的人,行船的人,他们的智慧和勇气,依然通过古船传递到了今天。小时候,我们在开元寺跑出跑进,没有在意大雄宝殿两侧的那副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现在想来,“圣人”不仅仅指那些大儒名士、得道高僧,也应该包括各行各业的手工匠人,和这样航海的商人和船员。他们也许迫于生计,也许心怀理想,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奋斗精神、惊人毅力和过人技艺,已经使他们超凡入圣。正是他们,使泉州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起点,和这条美丽航线上最光彩夺目的一颗明珠。他们,还没有资格被称作“圣人”吗?
这个“满街都是圣人”的城市,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名港,在她的全盛期,和近百个国家互通海上贸易,东至日本,南到南海诸国,西达波斯、阿拉伯、东非,以我们的丝绸、瓷器、茶叶和各种日用品,去换回异域的香料、药物和珠宝。在海上流动的不只是货物,还有人。阿拉伯人以他们对海洋的热情纷纷来到中国,带来了不同的宗教、文化和商业传统;中国沿海的人也纷纷下南洋,泉州因此成为中国重要的侨乡和华人华侨主要祖籍地。这一点,我有深切的体会。几年前,我参加中国作协访问团去东南亚,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发现那里的华人作家主要都用闽南话在交流。我忍不住也用家乡话和他们聊起来,结果,有一位当地的作家说:“你确实是咱泉州人,你的泉州话是鲤城区口音的。”我惊喜地说:“是啊,我是东街南俊巷的。”他缓缓地用无比地道的泉州话沉吟:“南俊巷,对,在承天巷边上。”那些我家乡的先贤,那些敢于冒海禁闯天下的平民百姓,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借着季风,乘着洋流,按照梦的指引或者神的启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播撒出去,在远处的岸上扎根,抽枝散叶。
我的三伯父潘曙澜先生,便是那些蒲公英先人的追随者,他大约在1936年下南洋,到了吕宋一家木材行当学徒,经过了我未必能够想象的艰苦奋斗,他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木材行,于是给爷爷奶奶固定地寄钱,成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父亲的家庭出身并不常见,在其他省份甚至会显得奇怪——“华侨工商业”,就是因为主要生活来源来自海外。当我父亲在政治、经济、家庭变故的几种困境中,奋力考上远在上海的复旦大学之后,面临的却是没钱上大学的压力,求生和求学的愿望驱使他给在马尼拉的三哥写了求助的信,信寄出去以后,他非常忐忑,几乎几夜白头,终于三伯的电报来了:支持上大学。当然,这不是一句空话,一切费用就要由这个哥哥来承担了。一个心比天高、天份也高而命运多舛的少年就此冲出了大山和愚昧、暴力的重重包围,来到了上海,迎来了属于他人生的阶段性的海阔天空。我们全家自然一直都感念三伯的爱心、担当和慷慨。但今天想来,要感念的还不止三伯一个人,若没有那些有勇有谋的先人闯出了这条路,若没有让人可以勤劳致富的南洋,那我父亲的命运就将彻底改写。简单一点说,如果没有海上的这条路,父亲的困境会演变成灭顶之灾,世界上根本不会有我这个人,侥幸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此刻以一个泉州人的身份为泉州和大海奋笔疾书,眼中噙着感怀身世和知恩难报的热泪。
图片:吕波
多少福建人,多少泉州人,都深深受惠于这条海上之路,这条祖先开辟、船过无痕的路,这条用生命、胆气、勇气、智慧开拓出来的路。没有这条路,哪来的侨乡?哪来的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外汇?哪来的困难时期救苦救饥救急的食品、衣物、日用品、药品?我母亲的二姨,我们一群孩子都叫她二姨奶奶,早年嫁去了新加坡。但是,在十几二十年里,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十分特殊而重要的存在,她给我母亲的整个家族不知道寄来了多少东西:面粉、饼干、糖、炒面、面干、奶粉、尼龙刷、尼龙袜,还有二手衣服,那都是她的孩子们嫌不时兴了不肯再穿的七八成新的衣服……一箱一箱,一包一包,一批一批。不但使我们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少吃了许多苦,而且给整个家族带来了精神上巨大的支撑——我们有外援。
祖先的福泽,几朝几代之后,依然在庇佑着我们这些后人,而我们这些后人,是否对得起祖宗先人?我们的奋斗和成就是否无愧于他们、无愧于刺桐的光荣?在古船面前,我无言以对,百感交集。
图片:吕波
既然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繁华和荣耀,却为何暗淡?何时开始消散?明初,朝廷为了孤立盘踞在沿海岛屿上的元朝残余力量,实行海禁政策,明太祖严令:“沿海民众不得私自出海,不得私通海外诸国。”而清初,清廷为了对郑成功实行封锁,进行了更严厉的海禁,顺治十八年还下旨“迁界”,强迫离海30里以内的人民内迁,村庄、田舍、船只,一律烧毁,制造了沿海30里的无人地带,并严令:“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
泉州港由盛转衰,往昔的繁华有如一梦。但民间的需求不可能被扼杀,因此,海上贸易转为民间的走私性质的私商交易,并且相当活跃;同时,被海禁、迁界、倭患的几重迫害,使得沿海的民众民不聊生走投无路,许多泉州人只能挥泪离乡,冲破禁令、冒死过海,这就是明清两代大规模海外移民潮的原因。许多泉州人就此侨居海外,今天他们的子孙已经成了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公民,中国不再是他们祖国,而成了他们的祖先国。
以至于后来,“Zaitun”在西方都成了未知之地,究竟是中国何处都争论不休,直到20世纪才由日本学者桑原骘藏重新考证出来。年,中外学者组团来到泉州考古调查,惊叹不已,泉州在世界学术界重见天日。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出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队来到泉州,认定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由此也认定中国是世界海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这些认可,在一个泉州人听来,竟如同晚年驻锡泉州开元寺的弘一法师著名的遗言一样“悲欣交集”。
当年,泉州城,刺桐港,不需要任何认定。她的美丽、富庶、繁华、自由,她的华洋共处、八面来风、文化交融、各得其所的宏大气魄,足以证明她自己。马可·波罗在游记里这样写道:“到第五天晚上,便到达宏伟美丽的刺桐城……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比马可·波罗晚到泉州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则说:“这是一座巨大的城市,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就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停有大艟克(船分三类,大者为艟克,中者为艚,小者为舸舸姆)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该城花园很多,房舍位于花园中央。”外国人居住泉州,保持着各自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习惯,也影响了泉州的文化氛围和人文性格。在泉州城里,生活安逸富足,环境美丽舒适,人们各信其信,各行其道,这是一座开放之城,自由之城,光明之城,梦幻之城。
电视纪录片《瓷路》中,对泉州市舶司遗址有浓墨重彩的描述,而这样的遗迹,在泉州仅仅被列为市级文保单位(编者注:年增补为省级文保单位),被列为国家级文保单位的竟然有31处(编者注:目前增至44处):万寿寺、六胜塔、九日山祈风石刻、天后宫、开元寺、清净寺和洛阳桥……它们,都默默地诉说着曾经的辉煌和历史的教训——亲海则兴,禁海则衰;自由则富,禁锢则贫;开放则强盛,闭关锁国则败亡。
颜英婷
泉州的人文性格是深受海洋文明影响和渗透的。相比于占据中国主流的黄土文化的安土重迁,追求安定,以农为本,重义轻利,重儒轻商,海洋文化是蓝色的:敢于冒险,积极进取,乐观勇敢,勇于拼搏,重儒亦重商,有良好的商业头脑和讲信义的经商传统。
万历《泉州府志·风俗》中云:“濒海之民,多以鱼盐为业,而射赢牟息,转贾四方……出没于雾涛风浪中,习而安之,不惧也。”这就是海洋性格和海洋文明带来的生活方式。
写到这里,抬头看到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正在播出《铁甲舰上的男人们》,里面的主角之一尤木友跪在海边礁石上喊道:“不是那个年代了,祖宗!”连续几星期浸泡在泉州沧桑之中不能自拔的我,竟然触景生情,泫然泪下。
海洋是美丽的,无边无际的,海洋性格是心胸开阔的,自由奔放的,积极进取的,敢为人先的。黄土文明一诞生就像一个中年人,而海洋文明始终是阳光灿烂、活力四射的少年。当中国被那个中年人紧紧抱住的时候,活力就会衰减,久而久之就会虚弱,而只要挽起那个少年有力的胳膊,就会快速向前,并且在大踏步前进之中越来越血气充盈,充满力量。
大海无言,有如忍耐;大海依旧蔚蓝,正如希望永恒。“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大词字字千钧,不是轻易可以重提的,祖先注视着我们,明天注视着今天。
图片:吕波
本文选编自《开放与守望——文学名家看泉州》一书
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