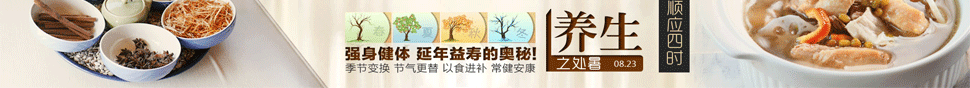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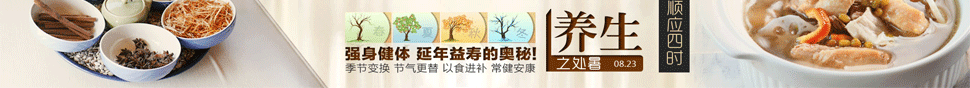
夏天敏,中国作协会员,昭通市作协主席。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曾在《当代》《十月》《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余万字,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名作欣赏》《中国中篇小说精选》《1年中篇小说精品集》《中国30年改革精品集》《鲁迅文学奖作品集》《新世纪获奖小说精品大系》《小说月报获奖作品集》等书刊选载。获第四届云南省政府文学一等奖,1年《当代》文学拉力赛总冠军,首届梁斌文学奖一等奖,《人民文学》“爱与和平”中篇小说一等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首届绽放文学艺术成就奖。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好大一对羊》在法国、美国、加拿大分别获奖。同名电视剧八集获“飞天奖”“金鹰奖”。长篇小说《极地边城》获中国作家“剑门关”文学奖。已出版长篇小说《极地边城》《两个女人的古镇》及散文集、中短篇小说集14本文学专辑。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文、韩文版在国外发行。
佳作悦读
星星点灯
夏天敏
大沙沟既是渠道,又是道路。洪水天洪水汹涌,滚滚而来,四逸而去,其他季节,就是道路了。我们都喜欢赤着脚在大沙沟里走路,大沙沟里的沙又厚又细又柔,脚踩上去,细沙朝四周喷涌,像踩在柔软的地毯上。其实,那种舒服劲儿,不是地毯之类能比的,那痒酥酥、湿润润、细腻舒适的触感,是很难以言喻的。
大沙沟周围,是一片很大很大的树林。树林是杂生树林,有很高很高的细细的白杨,有身躯硕大、胡搅蛮缠的刺槐,有亭亭玉立、羞羞涩涩的野桃花。还有粗糙皲裂、傻大黑溜的栗子树以及许多灌木。于是,这树林就参差不齐、错落有致了。
有高大的乔木,有低矮的灌木,有纷披茂密的草丛,就有枯草落叶。年代久了,这树林里枯草落叶铺了厚厚的一层,走上去很有弹性,按并不新鲜的比喻仿佛是棉垫子。树林蓊郁封闭,腐殖土厚实,容易养活各种小动物、小昆虫。大点动物是见不到的,小松鼠、小刺猬倒见得着,更多的是各种叫不出名的小昆虫,尤其是萤火虫,这树林里简直多得不行。太阳落山,夜幕降临,不远处的几座大山融入夜色,连图画似的几条线条也被吞噬。这时的树林里以及树林外的田野里,到处流曳着一丛丛、一簇簇或者星星点点的萤虫。树林里是小孩子不太敢进去的,里面的萤虫更是密不可数。有的成群结对、铺天盖地而来,有的一串串依附于树枝上、叶片上或者韧劲十足的茅草上,一动不动。夜风习习,枝叶晃动,茅草摇曳,点着萤灯的萤火虫像节目的彩灯装饰着树枝、叶片、茅草,使树枝、叶片、茅草显示出清晰的轮廓,流光溢彩,美妙无比。
童年时,我寄住在这个小山村的一家亲戚家。在这里,我享受着大自然最美妙、最神奇的馈予。每天随了村里一群光屁股的伙伴到处去玩,有时去禾荫翠绿、涟漪轻漾的水田里捉泥鳅;有时去小河边的地里偷摘青蚕豆;有时用泥拦坝,将清浅的小河切断,用盆将堤里的水舀干,剩下噼哩啪啦、乱蹦乱跳的无数的小鱼,再用撮箕撮出,洗尽晾干,用铁锅煎熟,蘸上盐吃,那味道的鲜美是不用说的了,村里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长得很美丽,细高细高的身材椭圆形的脸庞,精致、灵巧的五官,扎着一对羊角辫,虽然穿得很土俗,也就是染成青色的土布对襟衣,却剪裁得体、洗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个水灵灵的女孩儿,这么一个有着一双大眼睛的姑娘,却是个盲童。她那大而空洞的眼里,什么也看不见,世界在她眼中什么也不存在。但她却很爱美,她家的小土屋被她拾掇得干干净净,纤尘不染;没有上过漆的桌子、凳子,被拭擦得露出本色的木纹。她还从山坡上采来一丛丛的野花,用她父亲喝完酒的酒瓶插上,尽管她看不见花的颜色,辨别不清花的形状。走进她家的小院,你由不得被她强烈的热爱生活的劲头所鼓舞,由不得地被这种美的氛围所陶醉。
她不能任意地奔跑,她很想随小伙伴一起去捉鱼、去捕蜻蜓,但小伙伴们嫌她碍事,常常将她甩掉。她很伤心,也很孤独,孤独使她越发喜爱大自然。她常常一个人悄悄地出去,山村坡陡路险,到处是沟坎,明眼人稍微不慎还会跌倒,她常常被荆棘刺破手脚,常常跌得鼻青脸肿,家里的人见了很难过,她的母亲不知流过多少次泪,但她却乐呵呵的,啥事也没有。
在有明月的夜晚,我到她家的小院里去纳凉,和她说了很多很多的话,讲一个城里孩子对农村景物的感受。特别是沙沟旁树林里的萤火虫,我讲得绘声绘色、讲得很动情,我向她描述了树林的形象、色彩,向她描述了流萤的光亮、流萤的美丽,描述了空气的透明流动。最使她神往的,是那有着小小萤灯的萤火虫,那在静谧里、深邃的夜空里流动的灯火。她竭力地想象着萤火虫的美丽。眼睛看不见的萤火使她魂萦梦绕,日夜思念。她时刻跑来缠住我,要我带她去捕捉萤火虫。我知道沙沟旁的树林里坑洼遍地,荆棘丛生,白天进去还须小心翼翼,夜晚进去不光危险,还使人害怕。我除了跟其他小伙伴去过一次外,从此没有去过。
被她缠得烦了,我开始躲她。但她总能找到我,找到我后一会儿从衣袋里捧出一把果子,一会儿拿出其他吃食,央求我带她去捉萤火虫。我再也不忍看见她失望的神情和怏怏走去的孤独的瘦小的背影,我答应带她去捕捉萤火虫。天黑的时候,我们偷偷绕过大人的视线,向大沙沟走去。夜幕低垂,岑寂无声,使人感到害怕,她却走得极快。到了,沙沟边,我让她在树林外等我,她却坚持要去,说怕我也害怕。我捏着电筒,拉着她高一脚低一脚地朝树林里走。有好几次,她被土坑绊倒,膝盖擦破了也没吭声。有好几次她被长长的倒钩刺刺得直咧嘴,也忍住没叫一声。我将她安置在林中空地坐下,就去捕捉萤火虫。我捕捉得很认真、很投入、很忘情,我知道我是在为一颗美丽而孤独的心去捕捉萤火虫的。我忘记了害怕,忘记了夜鸹子的啼叫,眼里、心里只有萤火虫。树林里的萤火虫太多太多、太美太美,成串成串、成簇成簇,像银河里的星星,像流动的陨石,像节日的火把,像孩子们手里的小橘灯,美丽得叫人心悸。不知跌了多少跤,不知被树枝、荆刺钩过多少次,我终于捉到满瓶的萤火虫。萤火虫在玻璃瓶里射出的绿萤萤的光,几乎可以看书识字。
回到村里,我们偷偷溜进她住的小屋。小屋简陋而素净,木格子窗糊着白色的棉纸。她的小床上笼着一床白布帐子,那时还没有纱布帐子呢。我们将瓶里的萤虫放到帐子里去,那些小小的生灵极有灵性地飞出小瓶,有的匍匐于帐顶或帐子的四周,于漆黑中放出萤萤的亮光,极像点燃的星星,闪闪烁烁的,美丽得出奇;有的萤火虫在帐里飞来飞去,有的划出美丽的弧线。这星星点点的光亮,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愉快地飞翔。
房屋断想
房屋的诞生恐怕是随着人类的诞生而诞生的;房屋的进化,恐怕也是随人类的进化而进化的。人类无论是在树上筑巢而腾,还是以天然洞穴为居,总离不开寻找一个遮风蔽雨、寻求安全和温馨的梦想。房屋对于出身贫穷、低贱的我来说,留下了一串串心酸的不堪回首的记忆。
那条叫炭市街的长街现在是很繁华很热闹了,因为是在小城腹地的老街,房屋依旧是原来的老房屋,新的建筑很少见到,只是市场经济的勃然兴起,使这条街成了一条布料街。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家居住在这条街中段的一幢破烂不堪的房子里。确切地说,是居住在街面之后的一个小天“井”的小房子里。这个天井的形状很奇特,大井横有几丈长,宽却不足一丈,成了狭长的条形天井,且我们住的那间房的“天井”确是盖了瓦的,是有盖的天井的了。房屋高而天井小,光线就非常的微弱,我们住的那间房是永远晒不到阳光的。这样的格局,据说是解放前退街而形成的。要进天井,必须从一户人家通过。这户人家以及房屋的主人,和我的父亲都有亲戚关系。房屋的主人是我父亲的姨孃,也就是我们的姨奶奶。而前面这家的主人,是姨奶奶夫家的妯娌,我们称十奶奶的。姨奶奶家解放前很有钱,解放后自然败落了,留下姨奶奶和她的独生女儿,我们叫秀婊孃的独自生活。父亲是她的侄儿子,就借住在她家侧边的这间房里。这房子给我的印象是终年黑黢黢的,房子是土木结构,空间较高,门扇板壁被终年的烟灰熏得漆黑,阴天时,滴着乌黑的“烟子水”,这种水滴在衣裳上是洗不掉的。几间房的楼上都空着,因为楼下没有板壁,堆满瓦砾,通花照亮,是住不了人的,即使住人,也只能择其不漏雨的房顶一角。我的外婆因房紧就一度住在楼上的一个角落里,风冷霜大,一夜夜地咳到天明。楼下的前面,是所谓堂屋,没有窗子,只有两扇一丈多高的条形的破门。在没有钥匙的时候,我们就从门缝里钻进屋去,舀些冷饭吃,吃完又钻出来,到街上去玩。堂屋侧是条通道,也就是小巷巷,通到屋后的一间偏厦,那里是姨奶奶家堆杂物的地方,也是厕所。因此,我们家的房间后墙面临着厕所就堵了窗户。那个房间永远是黑的,不分白天黑夜都伸手不见五指。堂屋和房间的地面是土地面,永远的黢黑永远的潮湿。潮湿的地面上隔一段时间就会起一层圆圆的肿瘤样的土疙瘩,有铲脚泥的来了,请人铲去,不久又有了圆圆的肿瘤,地面也越铲越低,房顶倒越来越高了。住这样的房子,对于幼小的我们,最大的感觉是恐怖。天一黑,我们和母亲、外婆围着“鸡罩”烤火,“鸡罩”上永远烘着我们的衣裤和弟妹的“小片”之类。煤油灯被黑暗吞噬得只剩下一圈晕黄的光环,所有的板壁和门缝都是漏风的,无法确定的声响,时刻刺激着我们的神经。这时我们的头都依偎在大人的怀里,连抬头看一看的勇气也是没有的。所以,大跃进时母亲去食堂做炊事员通宵不回,外婆也去做活,我们宁愿像寒风中的麻雀蜷缩在街上的檐口下,也不愿回家,以至于后来我们蜷缩在一个大衣柜里而觉得有了安全感后才不去蹲街檐角。
在这个地方,我最渴望的就是生命的绿色。几棵秃了顶的槐树,永远蒙着厚厚的灰尘,蓬头垢面的了无生气,令人生厌。在我们那个天井的石缝里,不知什么原因,偶尔有菜籽发出的针尖般细瘦的芽。但这芽是永远长不大的,石板缝太细,阳光太少,即使窜出一点,也会被人的脚跟碾碎。我精心护侍的几棵菜芽,也被脚跟碾碎了,在石板上流出了细微的绿色的血浆,令我很是难过了几天。后来,我在一条小巷的墙角发现一棵苦楝子树苗。那时,小城的孩子流行的游戏是弹苦楝子果果,它跟玻璃球一般大小,只是没有玻璃球圆润光滑。玩的方法是互相碰击,击中对方即赢。这种游戏看似简单,难度却大,地面凸凹不平,要击中对方很要些本领。那棵苦楝子树大概是被谁遗忘了而被泥土压住生出根来的。我小心万分地将小小的树苗掘出,拿回家去却苦于没有地点栽。动了许多脑筋,翻出一些碎砖,在我家那盖了井盖的几尺宽的“天井”里垒了个土台,将树苗种了进去。以后的许多天,我一天到晚都去观看它的生长,结果非但没长大一丁点儿,倒渐渐枯萎了。其原因是很简单不过的,这没有阳光的天井,是任何植物都不能生存的。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也是会枯萎的。我后来患过脑膜炎、结核等病,我想和这黑暗、肮脏恐怖的环境是有关的。
过了一些年,我们一家又去租别人的房子住。这座房子比我们原来的房子好得多了,它是过去一家地主的房子。这户人家在小城是旺族,出过许多有名望地位的人。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这户人家没有例外地败落了。一个天井住了若干人家。这里房子虽陈旧了,却轩昂高敞,依着地势筑了高高的石阶,上面这排住的是汉族,下面这排住的是回族。一个天井回、汉人数大体相等。两个民族互相尊重,非常和睦。每当回族做礼拜时,总要炸些油香散给我们吃,只是住的人家太多,彻夜都有声响,与我们隔着一堵板壁的人家是铁匠,就在堂屋中间架了风箱设了铁砧打铁。他家打铁多在夜间,说是夜里凉快,我们整晚耳畔里都是叮叮当当的声音。起初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的,渐渐习惯了,也能酣然人睡。楼上住的这家就是房的主人,现在是彻底破落了,几个儿子均无工作,老太太是从昆明嫁来的大户人家姑娘,自然是横针不理、竖线不拿的。他家负债累累,借了张三的又借李四的,天天有人来要债,天天有人在楼上跺着楼板吵架,甚至打架。仅有的一点东西这个要债的来搬几件,那个来夺几件,不让抬就要打。我们住在这里最大的感受就是心惊肉跳,魂魄俱飞。尽管来讨债的不是向我们讨,但那薄薄的楼板上上演的一幕幕悲剧,却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在这里住了两三年,这家人经济状况好转时,强行将我们赶出来了。在这之前,他家欠了我父亲一笔钱,危难之中愿意租房给我们,以抵借债。
无房住的飘零感和受人驱逐的失落感,促使父亲下定决心买了间自己的房。经人介绍,我们终于买了一间十分低矮、异常破败的老房。这间房的两头,只有人高。就是说要上房去,只要手一撑就到房顶了。这房子很低矮,楼上的两头不能住人,只有中间部分有人高,勉强能直起腰来。楼板全变形了,凸凹不平,稍不注意就会绊倒。尽管如此,我们毕竟有了自己的房子,这使一家人兴奋了很长时间。那时我已十多岁了,早就渴望着能独自有张床,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我将这张床放到房屋中间与梁横齐,然后找了些木条、纸板把床和梁连接起来,又用纸板在那朽得连钉子都挂不住的椽皮上钉好。花的力气是难以言喻的,三伏天,小阁楼上热得赛蒸笼,房瓦晒得烫手,尘灰在流汗的脸上身上辣得生疼,人脏得像泥塘里爬出来的猪,但奇怪的是精神却振奋得很。白天晚上地干,终于将顶棚钉好,又用旧木板隔起来,糊上报纸,看来还真像个房间了。但这房间冬天太冷,上面是响瓦,北风无遮无拦地吹进来,躺在被里像钻冰窟窿;夏天热得透不过气,满楼都是一股烧焦的呛鼻的煳味。即使晚上,晒烫的瓦片依然发出余热,叫人辗转难眠。堂屋的地仍是土地,仍然潮湿;墙是一个人来高的快要坍塌的矮墙,墙下面半截潮湿得像孕妇样凸了肚子,颜色斑驳、污浊不堪。那段时间,我正痴迷于绘画,天天发了疯般。学的是中国画,画得稍好些时,就有了强烈的表现欲,想将自己的画挂在一堵雪白的墙上。想拥有一堵墙的念头折磨了我许久。想请人重砌那堵墙,请来一算,要10元钱,l0元正是我一个月的伙食费,自然开销不起。于是就自己动起手来,买不起砖头,到处寻找残破的半截砖,几经搜罗,在穷街陋巷中终于捡到足够的砖,于是拌沙和泥,现学现用。砖缝是要错位的,口面要整齐,苦于不是好砖,口面要整齐就颇费工夫。连夜连晚,累得人像一滩泥,干得十分的投入,十分的痴迷,终于将墙砌好,又反复若干次,终于将墙抿平。抿墙是技术性很强的活,不是这里高了,就是那里凹了,甚至会堆成堵。刮了抿、抿了刮,楞是将一堵墙抿得镜样平。又买来石灰,反复刷了多次,将墙刷得雪样白。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一堵平平整整、雪白雪白的墙,其喜悦,其兴奋,自是难以言表的。当我将自己的国画作品贴在墙上时,歪歪倒倒的陋室增色不少,屋里多了光鲜、多了典雅和书卷气,也多了温馨、祥和、宁静的气息。那晚,连苦于生活、疲惫烦躁、不识一字的父母,也很高兴,在灯下反反复复地看那堵墙,反反复复地看那些画,搓手捻脚,不知怎样表达自己的感情。
漆黑、破败、简陋的家,因其有了追求,而变得有了生气,变得温馨和鲜亮起来。困顿潦倒、愁苦的生活,因其有了追求,而变得亮实、自如、豁达起来。房屋,那规格不一,层次不一,质地、档次不一的房屋呵。
清官亭,那棵柳树下
在“文革”后期那最阴霾的日子里,没有电影、戏剧、书报可看,没有足可让人放心的朋友推心置腹地交谈,人都快变成没有思维的植物人了。正在这时,我突然收到一封未署名的信件。信上说,在地区群艺馆办的刊物《新花》上看到我的诗作,很想和我交个朋友,探讨写作技艺,如蒙承许,请于星期六晚八时在清官亭水池旁的大柳树下碰头,方法是左手持手稿。看完这信,我心中忐忑不安,惶惶然而不知所措。那年头,人人循规蹈矩,对非份之事避之犹恐不及,特别是文字问题,更为敏感,稍有不慎,便有罹罪之虞。况且这接头的方法又太奇特,和电影上的特务差不多,我不敢轻易以心相托。于是,我将来信丢在抽屉里,暂且不理。
夜里,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也许是那信上的内容太奇特、太神秘、太刺激人吧。我起身取出信来重看。那信上的字遒劲刚健,铁骨铮铮。字里行间洋溢着豪放的阳刚之气。我猜想此人定是热血人,否则不会有此举动的。想想自己,也是堂堂男儿,不能叫人耻笑。况且那时我正以小学毕业的底子,狂热地热爱着毕加索和托尔斯泰。如有师可承,有友可从,何乐而为?
星期六,我骑车从鲁甸出发,到昭通时,顾不上旅途疲倦,直奔清官亭。大柳树下,散乱站着几个人。一位皓首老翁闭目凝思策杖而立,显然不是。一个纤巧娟秀、文静娴淑的妙龄女郎在悠闲漫步,翘首企待,显然在等待恋人。接着走来戴眼镜的青年,大约三十来岁,一举手一投足都是学问,但盯了半天,也不见他亮出稿子。我心里越发忐忑,莫非是有人设下圈套,诱我入网,脊背感到一阵凉气。我正拔腿欲走,见那女郎从挎包里拿出稿子,用左手握着。我“啊”地一声,惊讶不已,立即用左手拿出稿子。她平静地走过来,莞尔一笑,说:“如果没认错,你就是天敏吧。信是我写的,我想交几个文学朋友,你不会拒绝吧?”我瞠目结舌,那遒劲刚健、豪迈奔放的字,竟是这么个纤秀的人写的。我说:“这里太闹,换个地点谈吧。”她说:“还有一个人呢!”正在这时,仲文兄来了,我们是老朋友,见面就寒暄。他见我和一个女人站着,若有所思地说:“你们谈吧,我在附近转转。”他走到大柳树侧边,亮出了左手的稿子。我和她同时发现了,惊呼一声,立即走过来,欣喜地同时亮出各自左手的稿子。我们都笑了,笑得那样惬意,那样开心,笑出了眼泪。
乡场上,温馨的夜
乡场蛇样地仄列于红土高坡下,房屋皆矮小、黝黑。也有一两间无端地高出来,是所谓参差。沿街一侧有沟,平时旱着,到了栽秧季节,就活泼了一街的风景,燕子也凑趣,在低低的天际画了许多抽象的意境。
靠近乡场的街尾是王奶奶的小旅店,依然是麦草苫的顶,依然国画般的浓浓墨韵。房顶上有一片青青的麦苗,麦苗绿出春的灵魂;有几株包谷,叶片虽柔韧,却剑戟般在天空中凿几笔坚挺的刻痕。
王奶奶家住着几个固定的客人,草医邓伯伯、果技站的小王叔叔、父亲和我。王奶奶原是城里人,不知何故解放前就迁到乡场上。她素爱干净,人又善良、热心。虽是农家客舍,却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熨熨帖帖。土的地坪光洁得不见纤尘,几件旧的木质家具油漆早已剥落,却洗得露出白的木纹。尤其是墙角的那拢火塘,拾掇得干干净净,时刻跳跃着红红的火焰,使人觉得十分温馨。
草医邓伯伯孤身一人,客居在此。每到赶场天,他卸了门板,就在客舍门口摆起摊子。摊子上有一堆长的、短的、方的、圆的、奇形怪状的牙齿,这就是他的牙医广告。他人精瘦,黄眼鼠须,样子凶狠,实际却很善良。有的乡民拔了牙,付不起钱,他挥挥手,叫人家走了。有的领情,过后送来一只猪脚,半叶肝子,一箩核桃,他尽数拿出来,店里的人一起享受。他爱喝酒,醉了,野野地跑出去,大家就急得不行,分头去找,直到找着,搀着、扶着回来。
果技站的小王叔叔高大,人憨厚而耿直。他是在清亮亮的河边,被王奶奶的独生女儿小媛那甜甜的山歌引来的。他住在客舍里,却不会煮饭,牙医邓伯伯煮了他吃,以后就是小媛煮了。小媛人俊俏,做事干净、麻利。吃新洋芋的季节,她提半提箩洋芋到清亮亮的小河边去,把新洋芋用瓷片刮得玉石样光洁,然后在铁锅里放一勺清油,撒了细盐、花椒面,还未起锅,就香倒一屋人。邓伯伯吃得差点要找别人医牙。我吃得肚儿砂锅样圆,小王叔叔塞得嘴边鼓起两个包,憨憨地看着小媛嬢嬢笑。一屋的温馨,一屋的欢情。
最使人留恋的是小客舍温馨的夜。
一到夜晚,乡场上就寂寞无声了。只有狗的吠声,平添了乡场的寂静;只有白杨的摩挲,增添了夜的深沉;只有小河潺潺的流水声,将梦幻撒满乡场。
在春寒料峭的夜晚,王奶奶家的客舍里燃着一拢旺旺的炭火,火上坐着“噗噗”冒气的茶壶。一豆煤油灯火,摇摇曳曳,使屋里温馨而迷幻。邓伯伯啜着茶水,吸着水烟筒,向大家讲着百听不厌的《聊斋》。那时,我只有五六岁,既爱听他的故事,又怕故事里的神怪,听得汗毛直耸,直往大人怀里钻,却又缠着他不停地讲。于是就有一个个美丽的狐仙在茅舍里游动,上演着一个个温馨的志怪故事。
在楼道下面,小媛嬢嬢借口人多,独自生了一盆柴火。
柴火滚烫的火烬里煨着快风干的板栗,柴火边炕着喷香的洋芋。小媛嬢嬢和小王叔叔不知在那里讲些什么,总也讲不完。板栗的爆裂声阵阵传来,又甜又香的味道弥漫在空间。邓伯伯叫我快去吃板栗,又诡谲地眯着眼睛。爸爸不准我去,但经不住诱惑,我还是去了。这时我就看见小媛媛正涨红着脸和小王叔叔啃嘴呢。见到我来,小媛嬢嬢一把将我揽进怀里,剥又大又甜的板栗给我吃。小王叔叔窘迫地搓手。吃完板栗,小媛嬢嬢说你千万不要乱讲,明天我又炕板栗给你吃。我被又甜又大的板栗封住嘴,答应不讲,还和小媛嬢嬢勾了手指。
但我还是经不住邓伯伯的诱骗,把见到的都讲了。邓伯伯笑得山羊胡子一撅一撅的,他说小媛就是狐仙呢,你看,小王叔叔不是被媚住了。我觉得小媛嬢嬢倒真是美丽的狐仙,在这温馨的乡场上的小店里,有这么一位狐仙,生活不是更美好、更神奇、更有味么!
长篇连载
第期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