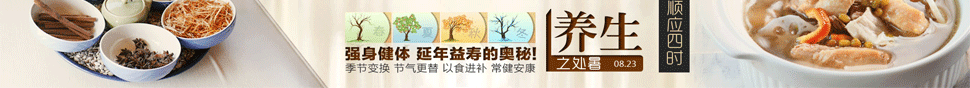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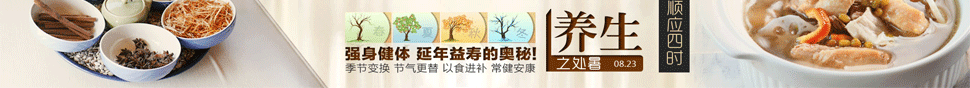
本文字数字,阅读约需15分钟
作者记录了一代女知青在庙前兰桥村的
劳作、生活点滴,值得仔细品读
作者:沃特玛(兰桥人)
年的夏天,一批刚跨出校门的高中毕业生,背起了行囊,告别了父母,来到连城县庙前镇的一个小村落——兰桥,开始了他(她)们三年艰苦的上山下乡知青生活。看着相片中的女生们在小溪里清洗着工具,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由左至右:叶艾莎,陈水玉,蔡建华,张云霞,
叶文华,张细萍
当年的兰桥没通水电,只有一条简易公路,一部手摇电话,一间小卖铺。全村人的油盐酱醋和生活必需品都靠这家小卖铺,小卖铺的挑夫每周去三十里外的庙前镇补一次货。我们和村民们一样,过着十分艰难的日子。加上公社分给知青点一块最贫瘠的田地,要我们给村民们树立榜样,让烂泥地里长出高产粮。更让初来乍到不懂农活的我们更是难上加难。
兰桥知青场原有知青16人,后来又来了两人,其中有九位15~18岁的女生,她们和男生一样,下田插秧,上山砍柴,时常是汗水、泪水满面流淌。夜晚,在小小的油灯下,她们会用各种方式打发着漫长的黑夜,从相互讲鬼的故事,到偷男生的手抄本相互传阅(当时没有正式发行的爱情小说,只有流行的手抄本),甚至肚子饿了还会偷吃当地人的贡品……
白天,她们也有无比欢乐的美好时光,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甜美的微笑,从田间地头的相互打闹,到组织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参加公社汇演,以及偶尔到附近矿区看一场电影。到了夜里,也时常为自己未来的前途落泪到天明。当年的她们都正值豆蔻年华,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喜乐忧愁与背后的泪水,她们用自己亲身的经历与青春汗水写下了一段精彩的兰桥知青的故事。
46年后的今天,她们通过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回忆,向我们讲述了许多当年鲜为人知的兰桥女知青故事......
当年的知青宿舍与女知青张云霞、叶艾莎、叶文华
《叶艾莎回忆》
年7月22日,我们一批从庙前中学高中毕业的同学13人和中学毕业的学生3人(最大的18岁最小15岁)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被安置在兰桥村,成为千百万知青中的一员,开始了知青生活的蹉跎岁月。记得在7月22日前几天,毕业班的许老师和曾老师陪同我们一道上兰桥,帮我们搬运床板,为每个学生搭床整铺盖。记得我在搬床板时,因道路窄小脚底不小心滑了一下脚被床板砸中,当时疼得直想哭,俩位老师见状赶忙上前将我扶起,并将我的脚搓了好一阵,才慢慢缓过劲来。
7月22日,我们坐着汽车正式来到兰桥村,当天所有的知青都有家长陪同,我母亲因病不能同行只好由大妹妹陪同。到了兰桥村之后在大队干部的引导下,我们来到了事先安排好的女生住所(见下图),当时有家长陪同的知青很快都找到了自己的房间与床位,而我和南娥(当时她也没有家长陪同)最后只剩下一间很小的偏房,房间内只能摆下一张1.2米的床铺,我们俩人只好同挤在这张床上。床铺是用稻草做床垫,上面铺上草席,放上家里带来的被褥,就算是将乡下的家安顿妥了。当时心里感到十分委屈,埋怨妈妈没能一同前来而大妹妹又没能帮上忙,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真想大哭一场。
兰桥村当时没有电灯,每当到了晚上,我与南娥都会将一张小木凳放在床铺中间,上面再放上一盏油灯,一人坐在一头,我们边织毛衣边讲着鬼的故事,时常有微风将油灯吹的一闪一闪,我们会被吓得蒙头钻进被窝。后来陈水玉、张云霞、叶文华也经常会到我们房间,围坐在一起听我们讲故事,传看手抄本,打发这漫漫长夜……
当年的女生住所已是人去屋空,
院内杂草丛生。(拍照:叶艾莎)
到了兰桥的第二天,我们知青就直接被分配到几个生产队参加双抢,我们带着镰刀,卷起裤管,下到水田里,学着农民的样子干起来。有一天我们参加割稻子时,蔡建华一不小心割到了无名指,只听她大叫一声,我亲眼看到一颗象花生米大小的手指肉掉在地上,真是十指连心,只见蔡建华疼的脸都发青,她的无名指鲜血直流,当时因为没有准备医药箱,只好临时用布条裹着止血。所以至今看到带齿的镰刀,我都还心有余悸。
当时乡下的水田里有许多蚂蝗,被叮上后腿上的鲜血是没办法止住的(吸多少血就流多少血),只能让它流着。同时一天下来,我们浑身上下都是被水稻叶子割伤的痕迹,看到满脸满腿满手的伤痕,加上被太阳暴晒通红的手臂,在汗水和田水的浸泡下,隐隐作痛,那滋味至今都记忆犹新。
不过,当时最开心的事情是帮生产队干活有点心吃,我最喜欢吃的是糍粑(一种用糯米捏成的饭团),每次都想下次再吃要多吃一碗,可是真到吃的时候,一碗都吃不完,糍粑太容易饱了,有时的点心是鸭肉煮稀饭,那时觉得可甜了,真是人间美味。
糍粑,是用糯米蒸熟捣烂后所制成的一种食品。
割完的稻子要打成谷子,用箩筐装好挑回生产队过秤,秤是一把单钩大秤挂在绳子上,再将装谷子箩筐挂在大钩上过秤。有一天我和云霞挑着谷子过秤时,我很好奇地想知道自己的体重,我双手抓着大钩同时将双脚勾起离开地面,让云霞帮忙看秤,称得体重是72斤(我当时身高有1.57米),按现在的标准是严重营养不良。但就是这样瘦弱的身躯,每次我挑稻谷的重量都会超过80斤,当时我与云霞都吐了吐舌头,啧啧,还觉得自己挺能干的。
当年我们亲手建造的宿舍,左边的平房(原先是食堂)
现在被改造成了车库。
参加完75年夏天的双抢后,我们开始建造知青场的宿舍,宿舍设计为两层楼,是自建的土坯房。我们每天挖土挑土,手起了血泡,肩磨破了,经历4、5个月的建造,我们有了一座挺像样并带有厨房、会议室和十个房间的两层楼房。男女生终于可以搬到了一起,女同学都住在楼上的3个房间,刘整作为队长住在2楼第一间,第二间是公社带队干部住,男同学住在楼下,就这样我们开始了集体生活,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生活变得很有生机。回想当年的生活是快乐的,虽然吃的是咸菜,大家还经常唱歌,打球。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女同学间的情感也开始产生微妙变化,那种不可言语的好感在悄然萌生,让我们产生了许多的好奇心……
自从有了自己的知青宿舍,我们开始过上比较正常的生佸,同时也需要上山砍柴,供厨房烧饭、做菜、烧水,当时帮我们煮饭的是一位军烈遗属,我们称呼她吉英姆。因当时食用油的供应很少,我们每人每月的半斤油根本不够用,炒菜时是用一块肥肉在锅里擦几圈,象征性地放了油,然后将菜倒进锅里煮熟。
当时每位知青每月国家可以供应一斤猪肉,每个月都会派人到庙前镇将大家猪肉统一买回来,并切成大块加入盐煮熟后用碗装好一人一份。当地的村民也需要将猪肉作为营养补充,但是并不是平时都有猪肉吃,因为养一只猪通常需要一年时间。一次,一位村民跟何世华说好了,下次知青点分猪肉时,他愿意用两只鸭子换何世华的一斤猪肉。可是到了分猪肉那天,何世华看到煮熟的肥肉便忍不住大口吃了起来,连饭都还没来得及吃,一口气将一斤猪肉吃个精光,等村民提着鸭子前来交换时,何世华的一斤猪肉早已下肚了。这村民十分生气地说道,他们一年干活很辛苦,想吃上一次猪肉的机会都沒有,可我们知青也正是长身体的关健时期又何尝不是需要营养啊!
到了春季山雨潮湿的季节,我们经常砍柴的后山会长出各种蘑菇,有牛肚菇、扫把菇、泥菇。有一天,我们好几位同学一同上山采了许多蘑菇,张云霞还采到一朵野生灵芝(有手掌心大)多珍贵啊,那天中午我们就用采来的蘑菇当菜煮了一大锅用来配饭,还真甜真好吃。但女生还是比较小心,怕会中毒吃得比较少,何世华可能是吃多了,当场竟吐了起来,将我们吓得不轻,云霞赶快拿出灵芝下锅煮水让何世华喝下,过后还真没事了,还算幸运。
还有一次,我们正在知青的田里插秧,有知青跑来说,河的上游有人用农药倒进河中毒鱼,男知青一听全都兴奋地跑去抓鱼了,还真的抓了一脸盆鱼回来,我们女生把鱼去鳞洗净后,要煮之前因没有油,官钦元在谢素珍的怂恿下把自己煮菜的一口杯花生油全都贡献了,那天大家可开心了有那么多的鱼吃。
为了增加知青场的收入,我们大家上山砍伐杂木棍,每根杂木棍有0.25元的收入,对当年兰桥村民十个工分才0.16元来说,这收入相当可观,每根杂木棍规格直径10—20公分,长2米以上,我们当起了伐木工,在山上寻找合适的树木,把它砍下去掉尾巴和旁枝,从山上一步步丢到山下,为了提高运输效率,我们学着伐木工利用他们铺好的竹编路,借来了伐木用的木驴,把砍好的杂木棍绑在木驴上,每架木驴可放10根以上杂木棍,我们前俩人后俩人一边一个把木驴往前推,木驴在竹编路上慢慢滑行,这本是伐木工干的活,需要力气和技巧,上坡需要力气往上推,下坡需要拉着慢慢下,拐弯时应掌握好前头不能冲出路面,后面要注意甩尾会将人甩出去,因杂木棍有2米以上长,在崎岖的山路上滑行,碰上拐弯时的难度可想而知,可我们这些不到20岁的男女知青竞能轻松自如地架驶这木驴在山路上行走。但意外也时有发生,一次在下坡拐弯时,整架木驴冲出路面,连同杂木棍和人摔下山坑,还好没造成伤害,算是幸运吧,现在想想都后怕。
遇到的一次最大的事故是去村口的山上烧火烧土,引起火烧山的事件。当时我们全体知青和兰桥大队村民出动救火,可那山火大得让人不敢靠近,我们没有灭火工具只能靠树枝打火,但拼尽全力也无能为力,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山火将整座山烧尽,山火烧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才自然熄灭了,因为山谷的河水阻断了山火的蔓延,才没有接连烧下去。第二天我们和兰桥的村民上山扫草木灰,挑回了许多草木灰也算是意外的收获。这次火烧山受到了连城县有关部门的通报,上边还专门派人下来调查此事。文华当时还开玩笑说,即使吃牢饭也比干这么苦的活强,最后这事也算过去了。
随着知青的陆续招工和上学的离开,知青埸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我们各自也都开始了自己人生中又一个崭新的岁月。
当年的知青宿舍与集体合影(后排左4:叶文华;后排左5:叶艾莎)
据叶文华回忆:
年夏天,未满18岁的我,高中毕业响应党的号召到庙前兰桥村上山下乡,翻开了人生的第一页。
后脚才跨出校门,前脚就踏入夏日炎炎的双抢劳动。记得我们16个知识青年(男生7人,女生9人),轮番到生产队抢收抢种。这些免费的劳动力各生产队都争着抢着用。(托李庆林给伟人的一封信后的福,第一年有国家补助每月8元,第二年有每月6元,第三年靠自己挣工分,比起早年的知青待遇要好的多了)。就这样我们投入农村和农民一起劳动。当第一次下水田收割水稻时,无数的青青小虫蜂拥而上袭击我们的双腿,被咬得又痛又痒。农民看了笑着说,你们细皮嫩肉的小虫最喜欢。这小虫在欺生,看农民黑黝黝的皮肤它不咬,专捡我们咬。当时我恨不得太阳快些将我们晒黑,和他们一样皮厚肉糙,这样就不会来咬我们了。想想现在的年轻人出门见到太阳要把整个人包得严严实实地防护起来,真是不同年代造就不同心态,造就不同的审美观。
那时候劳动真是越怕什么就越遇见什么。有一回拔完秧苗洗脚时觉得脚上还有一段寸长的黑色物体吸附在脚上,我用手搓它,摸一下它就往里缩,越摸越缩,我被吓得哭了起来。这软软的东西原来就是蚂蝗。我害怕极了,幸好有我心目中的小医生叶艾莎同学,她冷静地安慰我,并随手拔来了沟里的油草搓蚂蝗。这个怪物才不情愿地跑出来,害得我还流了好多血。记得那里的水田非常的冷,非常的毒,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女生个个细皮嫩肉,干完农活后脚都起了一粒粒的红疹,非常的痒。看着这丑陋的双脚,我们找来了碘酒一遍一遍地涂抹……到农村我身体产生了许多的不适,记得在赤日炎炎下劳作后,想要小便又尿不出,后来是小医生叶艾莎教我找些车前草煎水喝,很快解决问题,真是对症又神奇的中草药。我想若不是当年她招工进工厂,而是学习医术的话,也可能就是一位李兰珍式的名医了。因为她天性热情又好学,心细又认真,在医道上会成就一番事业。
农村生活的艰苦,药品又匮乏,靠这神奇的中药不知拯救了多少人。记得一次,我们村部召开大会,晚饭后我就感到腹胀腹痛,坚持不到会议结束就出来解手,刚蹲下就上吐下泻(应该是急性胃肠炎),与我同去的蔡建华看到这情况就陪我回到住处,然后打着手电筒去找鱼腥草,抓回一大把连夜用煤油炉煮了一大碗让我喝下。这草药真管用,服一次我就好了。在我内心深深地感激蔡建华同学,感激这神奇的鱼腥草。第二天,我又能活蹦乱跳地去劳动了。
在农村生活难免要上山砍柴,这是我最怕的活。一方面山高路滑还有蛇,另一方面一担柴装满了又挑不动,不满又会倒出来落满地,这担柴加上了我的汗水和泪水越挑越重……。劳动虽然艰苦,但是挡不住青春的活力,每次干完活,我想这下可能会累趴了,没想到一听说邻近的厂矿(锰矿八号点)有放映电影,马上有了洪荒之力,又能精神抖擞徒步5-6里地去看电影。农村的生活是那么的贫乏,夜晚是那么的漫长与无聊。我们几个知青常常会围坐在一起讲鬼的故事,听得起夜时一定邀伴一块去。就这样过着度日如年般的生活。期间也有许多美好欢快的时光,我们一起自编自演去参加公社汇演;整晚整晚边煮盐水花生边吃边聊天;渴了喝沟边的山泉水,而后又拉稀;月光下一起偷听别人谈恋爱;一起偷别人的手抄本小说传阅着……。在农村呆久了,逐渐胆子也大起来。记得有一次肚子饿了,见到夜晚外面有人拜神送鬼,有一碗米饭,一碗荷包蛋等。我们也敢把那碗荷包蛋端回来煮过吃了。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苦乐参半地到了年底,一块来的知青陆续内招参加工作,只剩下8位知青。这也是我最痛苦的半年多时光(我78年10月份考上闽江水电学校也走)。在还没有恢复高考的情况下,看着昔日的好友一个一个参加工作,我时常白天笑着,夜里流泪到天亮,想了许多许多……
有幸的是在这千军万马的知青大军中,我浑浑噩噩地度过了整整3年。当我离开兰桥时,村支部还送我一本笔记本,首页上写着“农村实践三年毕,迈步走向新长征”。就这样翻开了我人生的第二页。
当年兰桥女知青前后共有10人:张云霞、叶艾莎、叶文华、南娥、王爱英、蔡建华(已故)、陈水玉、张细萍、徐进、谢素珍
庙前那些事小编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yanshegana.com/ysgxz/10388.html


